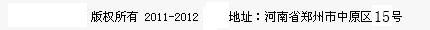写在前面
熟悉文章写作和发表的小伙伴都了解,目前涉及疾病诊断治疗标准的文章大致分为几个等级,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级别一:《XX疾病的诊疗建议或意见》,多是代表一部分医疗从业人员的实践总结和经验分享,要求无强制性;级别二:《XX疾病的诊疗指南或共识》,多是某一组织的集体意见发表成果,比《诊疗建议》的循证性更高,指导价值也更大,但要求仍无强制性;级别三:《XX疾病的诊疗规范或指导原则》,其结论多来源于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但是一旦应用了“规范”或“原则”这个词,就并非个人,小团体,乃至民间组织可以发布的了,因为它综合了诊疗的合理性和法规的限定性,就需要有官方机构进行背书。再说明白一点,如果实际的诊疗行为和前两个级别有所出入,但仍是遵循循证医学模式,或者至少有据可依,仍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如果和诊疗规范相冲突,则需要受到质疑。因为诊疗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法律效应。和社会法律一样,诊疗规范是规定某一疾病领域的诊疗行为的底线,不得随意突破。
近日来,无论是社会新闻还是业界的学术会议,肿瘤的规范化诊疗问题又成了讨论的热门话题。这里,我想起了年一度引发热议的“魏则西事件”,转眼间已经过去整整5个年头了,肿瘤规范化诊疗还面临着诸多问题。肿瘤规范化诊疗的重要意义自不必说,如能贯彻推行,无疑会最大程度地改善国民健康水平,也是国家《“健康中国”规划纲要》中重要的战略组成。若要在年实现提高整体肿瘤5年生存率15%的总体目标,规范化诊疗的实施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好了,目标明确了,那么我们面临的现状是怎样的呢?我国现在的肿瘤治疗的规范化程度又如何?
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和医疗行业的发展情况,中国目前的医疗规范程度还和欧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虽然这个差距正在被逐渐缩短,但综合一些市场调研报告来看,中国的肿瘤治疗的指南或者规范的遵从率仍然不容乐观。
笔者简单查阅了一下文献,发现这方面中国的调查研究还比较少。年《中华胃肠外科杂志》发表的《中国医师对结直肠癌诊疗规范和指南认知的抽样调查报告》中,中国医师对于NCCN结肠癌指南的遵循率在85%左右,对CSCO指南的遵循率在68%左右;年JCO发表的一篇关于人工智能支持乳腺癌治疗决策的研究中,中国医生对例乳腺癌的治疗选择与NCCN符合率基本在90%以上。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篇研究,并不是真实世界的患者实际治疗情况,而是更类似于给医生出题考试,让医生回答,不能反应实际治疗选择和指南的符合率。国外这方面的研究不少,年发表的一篇系统性综述发现:在欧洲乳腺癌诊疗中,总体的指南治疗符合率仅57.5%;系统治疗(化疗和内分泌治疗)指南符合率76%。美国的情况可能更差,只有50%的患者接受了指南推荐的治疗。
既然欧美发达国家的指南遵循率如此,人们不禁会问,是指南本身和现实诊疗行为有所脱节而导致的吗?并不是的。众所周知,以我国CSCO肿瘤指南为例,基本上是每年4月更新一次,而美国的NCCN指南则是按需更新。每当有重要的影响临床实践的循证依据出现,很快就会被写入NCCN指南并即时生效。以非小细胞肺癌指南为例,年NCCN指南有8个版本的更新,截止到今年4月份,年也有了4个版本,频率上基本上1-2个月就会有一次更新。
至于指南的价值,有美国一项大型的基于真实世界的研究发现,在16.7万肠癌患者中,接受NCCN指南推荐方案的患者的生存要显著好于没有接受指南推荐的患者。所以,遵循指南的规范化治疗会给患者更多的获益,这一点毫无疑问。
既然如此,我们就自然会问:那么如何看待那些不遵循指南的治疗行为呢?还是年的那篇系统性综述对于该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把原因归类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医生内部原因包括:不知道,不觉得有效,指南难以理解,倾向于有治疗经验的方案等;外部的原因包括:患者的年龄,肿瘤分期特性,合并症,生活质量,社会经济状态,前期治疗情况,医生的工作强度等。可见,肿瘤的规范化治疗,已经远远不是循证医学所能回答和解决的医学问题,而是更多的涉及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多层面的复杂议题。
以近年来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免疫治疗为例,多家企业生产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经在十数个瘤种上获得官方批准,解决了相当多的临床问题,但随之而来的更多问题尚没有确凿的证据,或者说各类临床研究正在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开展。譬如:NCCN和CSCO指南都推荐在III期不可切除的非小细胞肺癌同步放化疗后,使用抗PD-L1产品英飞凡进行维持治疗。然而,即使医院III期不可切除肺癌患者中,根据指南的治疗的比例也仅仅只有20.6%,大部分患者不是没有进行同步放化疗就是没有完成同步放化疗;我国也存在类似情况,部分原因是因为硬件条件达不到标准,医院,放疗所需要得大型设备购置和养护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患者又多倾向于一线城市或省会城市的诊疗。另外,抛去经济因素不谈,同步放化疗所需的流程长,时间成本高,很多患者和家属在等待的间歇期也不愿“干等着”,总要“做些什么”,而这些“情理之中”的选择,远不是指南和规范所能轻易改变的。
既然这样,如何开展指南未明确涉及,而实际诊疗中又的确需要的诊疗行为呢?卫健委年就牵头制定了《新型抗肿瘤药物合理应用的指导原则》,其中明确地规定了抗肿瘤药物在适应证内用药和特殊情况下用药的问题。
所谓特殊情况下用药,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超适应证用药,这是容易混淆,也是需要需要区别的两个概念。因为《原则》规定,对于在我国已经上市但未获批该瘤种适应证的药物,有以下两种情况的都可以使用该药物治疗这一肿瘤:一,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监管部门已经批准该药物治疗这一肿瘤的适应证,可参考应用;二,国际上已有大型Ⅲ期临床试验结果证明该药物对这一肿瘤有疗效,且被国际权威指南推荐的,也可以参考应用。这样的表述,为临床医生和研究者,同时也为标准治疗失败,面临无药可用的晚期肿瘤患者指出了一条明路,也客观上保护了新药研发企业的热情和活力,可谓一举多得,获益深远。
当然,特殊情况用药作为规范化诊疗的一部分,同样也需要强有力的监管。这方面,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可以作为参考。年大名鼎鼎的COCHRANE发表了一篇系统性综述,题目为“监察和反馈:对于临床实践和医疗结果的作用”。综述共纳入分析了个关于监察反馈对于临床实践影响的随机研究,然而研究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对于规范化治疗的提高比率只有区区的1.3%和4.3%。也就是说,监察反馈对于医疗职业行为的影响很少。整体的证据质量中等。文章同时指出,监察反馈可能在以下情况下最有效果:
1、医疗人员在一开始时的表现不佳;2、监察反馈的负责人是上级或者同事;3、至少要超过一次的监察反馈;4、要同时有口头和文字的反馈;5、反馈包括了清晰的目标和行动计划。以上均为参考,具体监管措施如何实施,还需要符合我国国情的调研结果作为基础数据,毕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何况监管了。
肿瘤的规范化治疗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但也是满载荣耀的道路,因为它会把更多的肿瘤患者引领向正确的方向。而作为领路人的医疗工作从业者,自然是任重而道远,其中少不了曲折和泥泞,除了有丰富的学识,还需要又坚定的信念和良好的医德作为保障。
魏则西的父亲在今年儿子5年祭的日子发抖音纪念,视频中夫妇两人通过试管婴儿而得到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可以走路了。父亲打出文字:则西,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没忘记你,希望来世你还来我们家。
我们不知道回家的路有多远,但为了回家,多远都值得。
参考文献:
BreastCancerResearchandTreatment():–